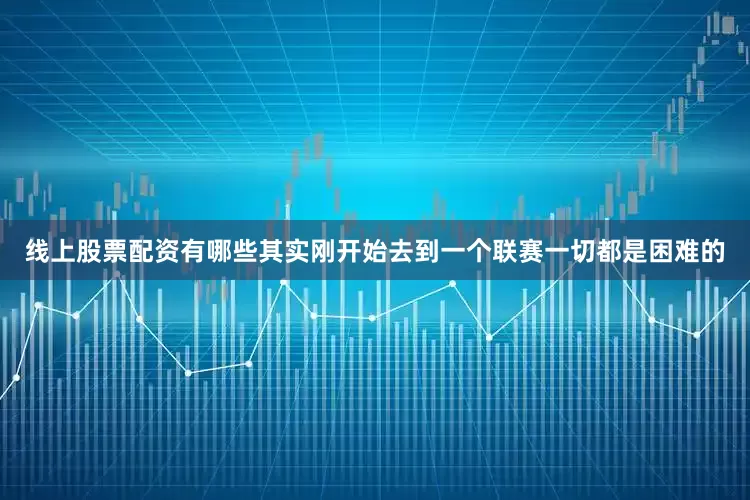1946年7月,大同城外的炮火轰鸣不绝,震得大地震颤。杨成武站在临时指挥所内,凝视着墙上的地图,眉头紧皱,皱成了疙瘩。
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跟晋察冀军区的战友们说,“十天肯定能攻下大同”,可是事实嘛,打了快一个月,城墙哪儿开了个口子都没有,真让人急得直抓狂。

更让人揪心的是,傅作义的部队正沿着道路绕到集宁去,显然是在搞“围魏救赵”那一套。那会儿的杨成武,可完全不是后来出了名的“翻身”,抗战那几年的他,在晋察冀可是个响当当的“招牌人物”。
1939年黄土岭一战中,他率领部队成功攻占了日军“名将之花”阿部规秀的指挥所,这一战一结束,便让“白袍小将”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华北地区。
1945年8月,他带领部队向绥远挺进,还接收了包头的日伪军投降。那会儿走到哪儿,战士们都乐意跟别人说一句“我们是杨司令的兵”。

内战的炮火一响,那份光荣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。大同—集宁战役,最后还是被迫撤出了包围,不光没攻下来城,还失去了上万名弟兄,一点土地都没有守住。
后来,毛泽东评这仗,说它是“战役指挥最糟糕的一例”。这话放谁身上都不舒服,特别是对一向打胜仗的杨成武来说,更是心里憋屈得很,后面还得受到不少挤兑。
同年十月,张家口保卫战打响,杨成武带着兵力死守,可傅作义手里的美式装备部队机动速度快得很,绕到侧面突袭,结果张家口还是失守了。
之后的易满战役和保北战役,结果都没搞出太让人满意的成效。

晋察冀的省会失去了,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,战士们私底下都闷闷不乐,吃饭时连碗都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
1947年头,晋察冀军区开了个高干会,杨成武站到台上反省,说自己“对运动战的规律掌握得不够,低估了傅作义突然快速转祸的可能性”。
台下坐的全都是老战友,眼里既有惋惜也带点质疑,散会的时候,他听到有人低声谈论,说“杨成武也就擅长打打游击战,大规模作战完全不在行”。

不太了解情况的人或许会认为,杨成武的作战能力退步了,其实不是这样,主要是战场环境变了,作战方式跟不上节奏。
晋察冀军区一直采用“军区—军分区—团”的三级体系,部队大多驻扎在地方,要搞大规模作战,调动兵力还得费好一阵子。
1944年推行精兵简政,把原来所辖的一分区给拆了,老部下们分散到各个部队,指挥链也就等于中断了。
再看看东北、华东的野战军,早就把纵队重新整编了,军区负责地方事务,纵队则专注于作战,效率别提多差了。

那时候,杨成武的压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了。他在回忆录里提到,那段时间经常熬夜到天亮,一闭眼就能看到牺牲的战友,一开会又是批评声不断,头发都掉了不少大把大把的。
原本想着靠老练的经验撑到最后,但后来才发现,游击战的招数在大规模军队对峙时根本扛不住,就在晋察冀部队快要吃不消的时候,中央调来了朱德。
1947年6月,朱老总一到阜平城南庄,没休息就马上召开座谈会,连续十天不停歇。
他最后定了两条规矩:一是重整野战纵队,叫做“军区负责地面,纵队负责作战”;二是让会打仗的人专心作战,别被地方的事儿缠住手脚。

这样一来,晋察冀的野战军就搭建起来了,杨得志担任司令员,杨成武则兼任第二政委和副司令员。朱老总对杨成武的支持,不仅仅是安排了个职位那么简单。
在清风店战役开打之前,朱老总陪着杨成武在地图前蹲了整整一下午,亲自指导他怎么“围点打援”,教他怎么计算敌军的行军速度,甚至把埋伏圈该在哪儿布置都讲得明明白白。
战斗一开始,朱老总每天都待在电台旁边,一听到前线传来敌人准备突围的消息,就立马让通讯员赶紧给杨成武发电,说“别怕敌人突围,放开口子让他闯”。
后来,杨成武跟身边人提起,说跟朱老总学一个月,效果比自己摸索三年还管用。光靠朱老总的指导还不够,杨成武还遇到个能跟他搭班子的伙伴,叫杨得志。

杨得志比他大三岁,红军那会儿就当师长了,打大仗的经验比他丰富得多。
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,两人的性格正好互补:杨得志沉稳,定了主意以后毫不慌乱;杨成武活泼,擅长突击和抓住关键时机。
当年在清风店打仗的时候,傅作义让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带着主力往北挺进,准备夹击野战军。司令部里意见分成两派,一派觉得应该继续包围徐水,另一派则建议撤回去打罗历戎。
杨成武当时就明确提出“打罗历戎”,还算了个账:“敌人离石家庄二百里,我这边离清风店一百里,谁先到,谁就赢!”杨得志听了也没多犹豫,立马拍板“就这么干”。那场战役确实打得精彩纷呈。

1947年10月17日傍晚,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掉头向南转去,杨成武率领前卫的三纵队,一夜之间奔了120里,第二天中午就攻占了清风店西南的合村,把罗历戎的退路彻底堵死了。
19日破晓,总攻开始,他亲自率领八旅攻占南合营,不到两个钟头就打通了缺口。到了20日晨,第三军军部和第七师全军歼灭,罗历戎也成了俘虏,一共俘获了一万一千个敌人。
这是晋察冀地区首次歼灭一个整军,朱老总还特意写了诗夸奖这场胜仗。

说实在的,这次胜仗不仅打回了部队的士气,也让杨成武扬了名。人家不是不会打大兵团,只是之前没走对路线,后来打的仗,杨成武越打越得心应手。
1948年11月,平津战役准备展开,毛泽东想到的办法是先“截断傅作义向西逃跑的路”,也就是说,先歼灭他的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。
杨成武带着第三兵团(后边改成第二十兵团)先去包围张家口,目的就是想把三十五军从北平引出来。
11月29日,他一举攻占了张家口外围,还歼灭了守敌一个师,傅作义果然慌了,赶紧调三十五军向张家口增援。

等到三十五军抵达新保安时,杨得志的第二兵团早就埋伏在那儿,瞬间就将敌人给包了个严实。杨成武又带着部队折返回来,帮忙把敌人牢牢地困在“口袋”里。
12月8日的总攻,他采取“先剥外皮,再掏心脏”的招数,先把外围的村庄攻下来,然后再往城里推进,十个小时不到就把三十五军的两万多人全歼了。军长郭景云也自我了断。更令人振奋的是张家口那场收尾战斗。
三十五军一没,张家口守城的孙兰峰带着五万多兵力打算突围,杨成武早就有了准备,把主力藏在城北的乌拉哈达和朝天洼一线,等敌人突进到一半时,忽然下令开火。

12月23日到24日,短短两天时间里,把那五万四千敌人全歼,结果孙兰峰领着几个人就跑了。这场仗后来被中央军委看作“歼灭战的典型范例”,杨成武在总结时只用四个字:稳、准、狠、快。
很明显,这会儿的杨成武,已经把游击战的机动灵活和大兵团的整体调度揉在一块儿,掌握得挺好的。
1949年1月,平津战役接近尾声,天津这块硬骨头难啃,守敌陈长捷带着十三万人,依靠坚固的工事,硬挺着说:“能守半年”。
林彪决定快刀斩乱麻,派刘亚楼率领五个军队去打天津,杨成武的第二十兵团负责从城东突围,目标是“断尾截断,汇合到金汤桥”。

1月14日清晨,总攻拉开帷幕,杨成武让四十六军担任先锋,没过多久,才三十分钟,就冲破了民权门外的壕沟,然后把主力全部投入战斗,沿着铁路线一路推进,直指市区。
到15日一大早,跟着从城西突进的第十九兵团在金汤桥汇合,天津就被划成了两部分。
到了下午,十三万守敌全部被消灭,陈长捷也被擒获了。打完这场仗,第二十兵团歼灭了三万八千敌人,自己这边伤亡还不到四千,成了攻城战的典范。
杨成武站在金汤桥上,望着迎风飘扬的红旗,心里暗自感叹:“从大同撤围到金汤桥,整整两年半的努力,咱们总算把局面扳回来了!”

1949年10月1日,杨成武站在天安门城楼上,担任开国大典阅兵的副总指挥,没人知道,两年前的他还在晋西北的寒风中写检讨呢。
这三年的翻身路,能走得通,可不是靠运气发挥作用,制度的作用可得说一声。
朱德把野战军重新组建,把杨成武从地方事务中“挖”出来,专门负责作战,这就像给有本事的人搭了个好平台,能把他的技能全部展示出来。
要是还像以前那样,又得管地方,又得管部队,两头拉扯,哪怕再厉害的本事都难以全都发挥出来。再说搭档的重要作用,也是不能忽视的。

杨得志的沉着稳健,加上杨成武的机敏灵活,合在一起就是“1+1比2还强”。打仗可不是靠一人扛得住的,得有人定方向,有人负责落实,俩人密切配合,【才】能少走弯路。最重要的,还是杨成武自身的作用。
从大同失利到清风店赢得胜利,再到张家口、天津的战役,他没把全部错都归咎于客观因素,而是一直在思考怎么把不足之处改进。
游击战的经验得记牢,但得把它融合到大兵团作战中去,除了勇猛,还得会搞统筹规划。

并不是说杨成武全靠别人,真正关键还是他自己总结教训的那股劲儿,就像我们做事一样,别人帮衬固然是个帮忙的机会,可要是不自己动脑子琢磨,那也白搭。
毛泽东后来评价杨成武,称他是“华北战场的后起之秀”,还提到“要看长远发展,不能只关注一时的成败。”
实际上,杨成武这段经历,不单单是一个将军的起伏记忆,更像是一个军队在挫折中不断成长的缩影。

人生走到头,也不可能一直事事顺心顺意。遇到低谷不要怕,真正怕的是失去那份反弹的勇气和用心琢磨事儿的心情。
杨成武用三年时间证明了,就算一开始被叫做“败军之将”,只要走对路、肯努力琢磨,依然能变成“翻盘名将”。
配资行业查询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软件app本作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
- 下一篇:没有了